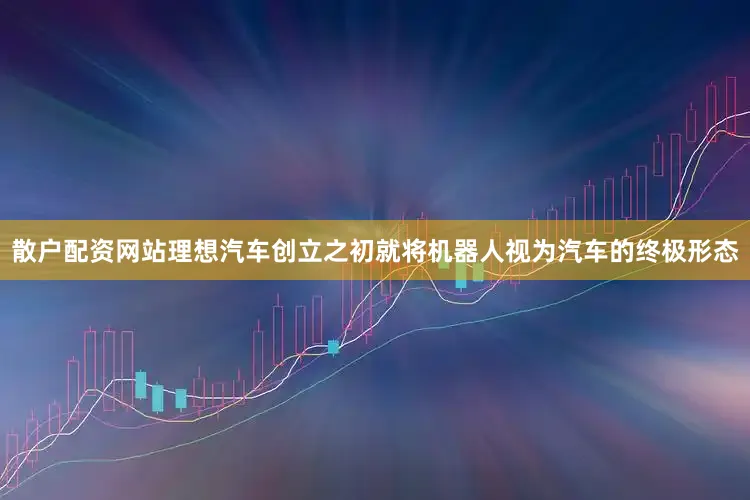1.
客厅里的空气浑浊得像发酵了一周的泔水。
廉价的香水味、中药熬煮后的苦涩味,还有那堆粉色编织袋散发出的霉味,混合在一起,死死堵住了我的鼻腔。
我站在玄关,手里握着那个24寸银色行李箱的拉杆,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婆婆正盘腿坐在沙发上,脚边是嗑了一地的瓜子皮。她斜着眼,手里拿着我的真丝抱枕垫在腰后,那是被她女儿赵悦刚随手扔下的。
“都要当姑嫂了,一点眼力见没有。”
婆婆吐出一片瓜子壳,声音尖利,“悦悦刚离职,心情不好,来咱家住一个月散散心。你看看那客房,跟猪窝一样,你也不知道收拾收拾?”
赵悦窝在沙发的另一头,低着头刷手机,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她的脚上,穿着我那双仅在室内穿的羊绒拖鞋,后跟已经被踩变了形。
展开剩余91%我低头看了看手表,19点30分。
“妈,我要出差1个月。”
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我在工厂车间里做汇报时一样冷静、机械,“公司急派,这一走就是30天。刚才下班回来,我只忙着收拾我自己的东西了,客房的事,你们随意。”
婆婆愣了一下,随即眉头倒竖:“出差?你那个破质检员的工作有什么好出的?悦悦刚来你就走,是不是存心给她甩脸子?你走了谁做饭?谁伺候?”
“推不掉,这关乎我的饭碗。”
我没有解释更多,甚至没有看一眼站在阳台上一声不吭的丈夫赵阳。
“兹拉——”
行李箱的拉链声在死寂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。那声音像极了撕裂某种粘连已久的胶带,干脆,决绝。
赵阳终于转过身,指间夹着烟,神色晦暗不明:“婉婉,必须去吗?”
我看着他,目光落在他无名指上那个光秃秃的位置,嘴角扯出一个标准的职业化微笑:“必须去。如果不去,在这个家,我就活不下去了。”
没等他回应,我拉起箱子,转身推门。
随着防盗门“咔哒”一声落锁,我将那个充满了算计和恶臭的空间,彻底关在了身后。
电梯下行的失重感传来,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我并没有按去机场的负一层地铁,而是按了去往市中心的一层。
这场“出差”,是我给这段婚姻留出的最后30天倒计时。
也是我为自己准备的,唯一的逃生通道。
2.
我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。
出租车穿过雨夜,停在了离家五公里外的一处短租公寓楼下。这是我一周前就订好的,付一押一,刚好一个月。
房间不大,只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。
我把行李箱推到墙角,没有打开,而是先从包里拿出一个平板电脑,熟练地连上公寓的WiFi,点开了一个黑色图标的APP。
屏幕闪烁了两下,画面亮起。
那是家里的客厅。
那个原本用来观察猫咪有没有按时吃饭的广角摄像头,此刻正无声地注视着沙发上的一家三口。因为角度隐蔽,藏在空调柜机的上方,他们从未在意过那个闪着微弱红点的小东西。
我是做食品质检出身的。
我的工作准则是: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瑕疵,因为那背后往往藏着致命的隐患。而在婚姻这场大型生产活动中,由于我的疏忽,直到一个月前,我才发现这批“产品”早已从内部烂透了。
监控画面里,我前脚刚走,婆婆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
“死丫头,终于滚了!”她冲着门口啐了一口,“悦悦,快,去她屋里看看,首饰盒在不在!”
赵悦扔下手机,一改刚才的颓废,像只闻到腥味的猫一样窜进了主卧。
几分钟后,主卧传来了翻箱倒柜的声音。
“妈!空的!”赵悦的声音透着气急败坏,“金项链、手镯,连个耳钉都没剩下!这女人是不是知道什么了?”
画面里,赵阳依旧站在阳台,像尊僵硬的雕塑。
我坐在短租房的冷光灯下,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红色的圆珠笔。这是我的职业习惯,随身带笔,随时准备在不合格的产品上画叉。
我习惯性地按压着笔帽,“咔哒、咔哒”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响。
他们当然找不到。
那些首饰,早在三天前就被我分批带出来,存进了银行保险箱。
包括那张存有我父母给的一半首付凭证的银行卡,以及我所有的证件。
我看着屏幕里气急败坏的婆媳,和沉默得像个影子的丈夫,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摩挲。指腹因为常年接触化学试剂和纸张,有些干燥粗糙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一个月前,也是这种触感。
那天我坐赵阳的车去办事。因为平时我都坐后排,那天却鬼使神差坐了副驾。在找纸巾的时候,我在副驾储物格的最深处,摸到了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团。
作为质检员,我对任何“异常状态”都有着天然的敏锐。
我展开那个纸团。
那是一张当票。
物品名称:铂金钻戒一对(含女戒)。典当金额:一万二。
时间是半个月前。
那一瞬间,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
我想起半个月前,赵阳突然说要把婚戒拿去店里做保养和款式升级,顺便把他的也带去。我还傻乎乎地夸他终于懂得浪漫了。
原来,浪漫的背面,是销赃。
我没有当场发作。在工厂里,发现重大质量事故苗头时,最忌讳的就是大呼小叫,那样只会让责任人毁灭证据。
我把当票拍照,然后原样揉好,放回原处。
这一个月,我像个潜伏的特工,不动声色地“抽检”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。
撕碎后扔在猫砂盆底下的快递面单,寄件方是某不知名的“信息咨询公司”;
赵阳手机里那个伪装成计算器的私密相册,里面截图全是各种网贷平台的还款日;
还有半夜两点,他躲在厕所里压低声音的嘶吼:“再宽限几天,我妹妹真的没钱了……”
拼图一块块凑齐。
所谓的“小姑子离职”,根本不是受了委屈。
赵悦染上了网赌。
那个窟窿,不是一两万,而是个无底洞。赵阳作为“扶妹魔”,已经把自己的积蓄、信用贷、甚至我们的结婚戒指都填进去了。
现在,他们把目光盯上了这个家里最后、也是最值钱的东西。
那套我们住的房子。
3.
“出差”的第三天。
监控画面里的气氛越来越焦灼。
客厅茶几上的烟灰缸里,已经堆满了烟蒂。我数过,一共26根,全是赵阳抽的。
平时他在我面前,总是表现得温文尔雅,连抽烟都会去楼道。现在,他终于卸下了伪装,露出了那副被焦虑和懦弱啃食得千疮百孔的真面目。
“哥,那边说最后期限就是这周五。”
赵悦坐在地毯上,手里抓着头发,声音带着哭腔,“要是还不上那七十万,他们真的会去单位闹的!那样我就完了,这辈子都完了!”
婆婆在一旁抹眼泪,一边哭一边数落赵阳:“你倒是说话啊!你是当哥哥的,难道眼睁睁看着你妹妹去死?咱家就悦悦这一根独苗……哎不对,就悦悦这一个闺女,你忍心吗?”
赵阳痛苦地抱住头:“妈,我能借的都借了。我的征信已经黑了,连高铁都坐不了。你让我去哪弄七十万?”
“房子啊!”
婆婆突然拔高了嗓门,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精光,“这房子现在的市值少说也有一百八十万。只要抵押出去,贷个一百万,不仅能平了悦悦的账,还能剩下一笔钱给你做生意翻本!”
赵阳猛地抬头:“那是林婉的婚前财产公证过的!房产证上虽然有我的名字,但大部分首付是她家出的,要想抵押,必须她签字!”
“签什么字!”
婆婆一巴掌拍在赵阳背上,“她是咱家媳妇,是你老婆!夫妻一体,你的妹妹就是她的妹妹。再说了,她现在不是出差了吗?那个什么委托书,你不会弄个假的?”
“这是诈骗!”赵阳的声音在发抖。
“什么诈骗!这是一家人互帮互助!”
婆婆理直气壮,“等生米煮成熟饭,钱贷出来,把难关过了。等她回来,咱们就说是给她妈看病急用借的,她那个软心肠,还能真把你送进监狱不成?再说了,只要悦悦以后不赌了,慢慢还就是了。”
屏幕外,我握着笔的手微微颤抖。
不是因为恐惧,而是因为愤怒。
极致的愤怒。
在他们眼里,我不是一个人,不是一个妻子,而是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血包,一个为了“家和万事兴”就必须吞下所有委屈的傻瓜。
他们赌定了我心软。
赌定了我爱面子。
赌定了我为了所谓的“婚姻完整”,会咽下这颗带着剧毒的糖果。
发布于:湖北省配资10倍的公司,配资投资服务,网上实盘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